

荒村之奠
李本深
这是个靠山的荒村,村里总共才几十户人家,地薄人穷,遇到灾荒年,连狗的吠叫也没精神。
这一年,日本鬼子进了中国,中国的土地上就四处都遭殃了。这天,村里忽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兵,先是叽哩哇啦了一阵,后来就在村里安营扎寨住了下来。这帮日本兵有个名头,叫什么”宣抚班”,领头儿的日本人像个劁猪的,有个怪怪的名字叫“麻虎一郎”,而麻虎这词在当地的老土话里就是狼的意思。麻虎一郎说他们来村里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什么“模范村”。
日本人住下来的头一件事便是散发洋火,这种红头儿的火柴好使唤得很,不管在哪儿一擦就能划着;二件事是给小孩子发糖果,一边发,一边还捏捏小孩子的脸蛋儿,拍两下;三件事发仁丹,人均得到了鸟屎似的几粒,含进嘴里尝尝,有凉飕飕的感觉;第四件事便是用白石灰水在村里的墙壁上刷标语,但村里的人多半不认得字儿,只有王六爷上过几天私塾,他认出日本兵在墙上写的是”大东亚共存共荣”几个字,但不知道这几个字究竟啥意思。那指挥日本兵写标语的麻虎一郎抬手指了指王六爷,又指指自己,然后竖起大拇指冲天上使劲比划了半天,王六爷懵里懵懂,最后还是默默地摇摇头,到底也不知道那日本人手势是想要表示啥意思。
荒村的日子看上去还是一如从前的安静,起先,天落黑的时候,总有个日本兵背了枪在村头站岗放哨,后来就连岗也不站,哨也不放了。
没几天,那帮日本兵就觉得无聊了。无聊了就灌了酒来喝。当地酿的老白干三杯躺倒人,劲儿大得邪乎。日本兵又没啥酒量,一喝便醉了,尤其是那个领头的麻虎一郎,醉得更凶.一边手舞足蹈着,一边呜哩哇啦地高唱了一阵日本歌儿,唱到高兴处,忽然心血来潮,嚷嚷说要开一个敬老会.叫村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统统去参加。
村里年事最高的是王六爷,起初想不去,可日本兵说不去不行,必须得去。王六爷就和村里几个老人蹒跚着去了。
“敬老会”是在日本兵住的那座堂屋里开的,麻虎一郎叫几个老人在桌案边坐了,丢了一堆糖瓜儿叫老人们吃,但又做出一项奇特的规定:不许用手抓了吃,必须直接用嘴巴吃,这还不算,还叫人捧了一捧生石灰来,均匀地撒在那糖瓜儿上。于是,一帮日本兵都奇怪地兴奋起来。
王六爷和几位老人互相望望,一张张脸上立刻都落了一层黑霜。王六爷嘴里没说啥,只是用白白的眼珠子直直地瞪着那满脸通红的麻虎一郎,嘴闭得铁紧。
麻虎一郎醉醺醺命令王六爷:”你的!米西米西!”
王六爷毫无反应,眼皮也没撩一撩,撅起了下巴颏。
麻虎一郎更大声地冲王六爷嚷嚷:”你的!米西米西的干活!”
其他几个喝得脸红脖子粗的鬼子也都来劲了,一齐”啪啪啪啪啪”有节奏地拍着桌子,大声起哄:
”米西!米西!米西!”
“米西!米西!米西!”
麻虎一郎见王六爷毫无反应,火了,趁着酒兴扑上来,伸出一只狗熊似的巴掌,将王六爷白发苍苍的脑袋往桌案上猛地一按,王六爷便满嘴粘了一层的白灰,模样看上去变得十分滑稽了。于是,那一个个日本兵都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,笑得前仰后合,拍腿的、搂肩的,乐不可支。
王六爷整个儿人彷佛冻住了,两只眼睛里只有白光,突然,从他嘴里低低地喷出一句当地骂人最难听的土话:“XXXXXX……”
日本兵听不懂中国话,再者又灌多了酒,因此只顾得望着王六爷沾满白灰的嘴巴狂笑如雷……
开罢”敬老会”的当天夜里,王六爷就自缢了,是吊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上的。王六爷的后人收了尸,停尸不葬,请了和尚念经,七天七夜,没想到第六天天明,“宣抚班”的那个麻虎一郎就没了踪影。一班日本兵急慌四处寻找,却有的落了崖,有的跌进了沤麻坑,有的光剩了一具无头的血身子横在野地里,野狗拖了肠肠肚肚乱窜……
等到城里的日本人扛了山炮、骑了洋马赶到村里来时,正碰上给王六爷送葬的人群缓缓地移动着,天地间一片缟素,吹鼓手呜呜地吹着唢呐,众人哀歌当哭.那送葬的队伍里,老的老,少的少,多半是老人和妇女儿童,竟没一个像是能杀入的壮汉。
村里的壮汉早几天都投奔八路军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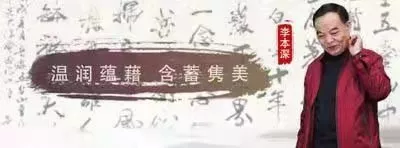
李本深,1951年生,山西文水武良村人。国家一级作家,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一期,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暨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。现为德商汇山西联盟名誉主席,书画院院长,八福康集团书画院名誉院长,数十年舞文与弄墨并重,著作有长篇小说《桃花尖》、《疯狂的月亮》、《敦煌之棺》、《灵魂的重量》等多部,他编剧的22集电视连续剧《铁色高原》曾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热播。他的小说《丰碑》被选入人教版小学五年级课本。李本深酷爱书法,至无书名而不慕虚华,沉溺翰墨而绝少交游,嗜墨如命且敬惜字纸。自号十八翁,云外庐主人。
编辑:李敏
责编:张剑利
主编:王生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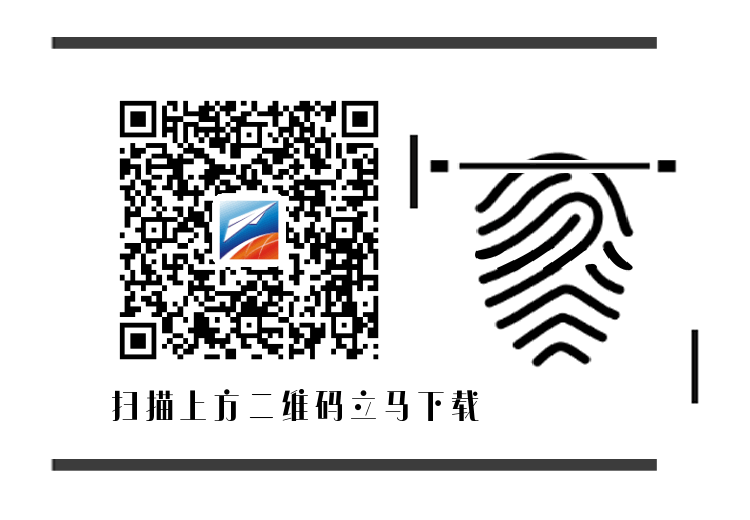
我要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