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维瑞和芮徳娜夫妇的生活,似乎只是一场无尽的饗宴。丈夫事业有成,妻子优雅聪慧,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小孩,一群迷人的朋友,还有一只狗和一匹小马。模范家庭,理想人生,却在几无觉察间如一艘大船慢慢腐朽,无可挽回……
从未有人这样写过被时间磨损的爱和婚姻,也没有谁如此心碎地写出家庭与自我、占有与放弃之间逐步扩散的裂痕。詹姆斯•索特精美绝伦的小说,将人生中那些不可磨灭的时刻酿成烈酒,一饮而尽。在他笔下,碎片具有了永恒的意义,而几个句子便足够最丰富重大的事件隐秘地发生。“一部20世纪的杰作”,《光年》是属于所有世代的理想的哀歌。
1975年,《光年》首版,奠定索特“作家中的作家”地位。
2007年,《光年》绝版多年后由“企鹅现代经典文库”重版。
2011年,《巴黎评论》授予索特“哈达达奖”并推出专题文学月,裘帕•拉希莉、杰夫•戴尔等一众名家撰文评述其创作。
2013年,暌违三十年推出新长篇,引起“詹姆斯•索特风潮”,这位“美国当代文学被遗忘的英雄”(《卫报》),始从文学界进入大众视野。
本文为《光年》一书的书评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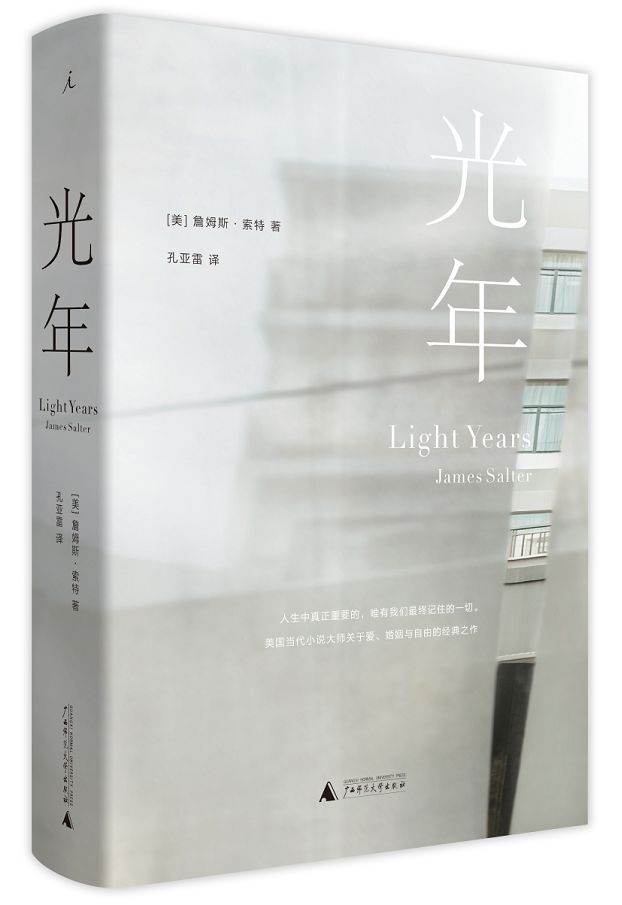
“维瑞,听这段。”那是关于马勒的丧女,她得了白喉。
“你干吗念这个?”维瑞问道。
“太可怕了。”她说。
这是小说《光年》中的情节,詹姆斯·索特写于七十年代。芮德娜爱看马勒的传记,兴起时还会念给丈夫听。不是作曲家马勒,而是他的妻子阿尔玛·马勒。
索特无法预知,该书出版的五年后,25岁的女儿搬去与他同住,会在洗澡时触电身亡。多年后的采访中,他还是会说,“我可以书写君主之死,但无法书写自己孩子的死。” 阿尔玛是可以书写自己孩子死亡的那种女人,而且不止一次。但无论可不可以被书写,丧女之痛是真实的。文学是人类的神经末梢,在不同代际、身份、性别的人之间传递着痛感。
Salter,生活就像盐,我们早已洞悉了它的苦难,却还是要自己一一体会。

“生于一次战争之后,另一次战争之前。”
1975年,艾伦·金斯堡刮掉了胡子,正在虔诚地跟随创巴仁波切修习藏传佛教;金斯堡还和朋友一起创办了杰克·凯鲁亚克精神诗学学校,以此纪念那位因酗酒过量死在了60年代结尾的战友;也是在他的帮助下,威廉·巴勒斯找了份大学讲师的工作,并顺利戒除了毒瘾,沉迷于写歌作画。皈依、殉道、修身养性,垮掉的一代三巨头各得其所。
而他们的同时代人,詹姆斯·索特,悄无声息地出版了他的第二本长篇小说《光年》,一场连最重头的离婚戏码都上演得如此寡淡的婚姻纪实,就像一束光没入白昼。那个夏天,令美国文坛沸腾的是《洪堡的礼物》,索尔·贝娄正值黄金年代,他的盛名被推向顶点,还要等到次年摘得诺奖。
索特是一个更像法国人的美国人。借一个欧洲人之口,传达了对欧美两地的印象:
“就像太阳在慢慢熄灭……像美国这么辽阔的领土和历史,是不可能消失的,但可能会变得黑暗。而看起来它似乎正在朝那个方向滑去……你了解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吗……问题在于,我们非常依赖你们。我们现在很弱小。我们已经完了。当然,我们还有回忆。”
除了地域归属的模糊,索特身上几乎也没有时代的印记。没有披头士,没有反越战,没有水门事件,没有滞涨,使他着迷的是不息的河流,而不是两岸的风景。一个普遍的理解是,索特是“反政治”的,他避免谈论速朽的时事,是为了更接近不朽,或者是本书中反复提及的“伟大”。
但这恐怕是对政治和索特的双重误读。
索特曾在采访中说过,存在是为了讲述,写作是为了被阅读。索特从来不等于离群索居、特立独行。他依然关心世界。只要还在读同时代人的书,就绝不能称之为避世者。在写《光年》的期间,福柯早就写出了《疯癫与文明》,德波也已经剪出了《景观社会》的电影,五月风暴的余波仍在回荡,“我们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!做一个现实主义者,争取不可能的事!每个人都有获得自由的自由。”忠于时代的焦虑和命题,而非事件和口号,这显然是更高的自觉与忠诚。
政治也不仅仅是战争与选举,那些巨大的权力化身为更加难以察觉的样子,指使着带轮子的巨型玩具熊和高端定制的衬衫代行其职。无论是在《游戏与消遣》还是《光年》里,日常生活中无处不是权力与反抗、占有与剥夺,譬如永无止境的性爱,譬如拒绝穿成妈妈喜欢的样子的女孩,譬如“睡觉时脚都不会碰到一起”的契约。
从来没有什么“在自己身上,克服这个时代”,只有“在这个时代里,克服你自己”。克服自己,意味着从日常生活中认出你自己,并自觉与之对抗。生活就像马的牙齿,它们会一直往外长,然后被磨掉。“如果她不吃,牙会怎么样?”“一定要让她吃。”
“生于一次战争之后,另一次战争之前。”“三十二岁,孑然一身。”这是维瑞,一个优雅的犹太建筑师丈夫。“她有张大嘴,一张女演员的嘴,迷人,光亮。腋窝里的黑点,呼吸带薄荷味。她天生不羁。”这是芮德娜,妻子。他们居住在一幢维多利亚式的大宅里,两个女儿,一辆车,两三个好友,一只狗,一只兔子,一群母鸡,一匹马。
丰美的中产阶级生活,徒有其表的婚姻,心照不宣的出轨,区别在于:维瑞的短暂出轨,是为了对抗自己对妻子的依赖,是自尊和焦虑的产物;而妻子接二连三地出轨,完全是出于对性和爱本能的需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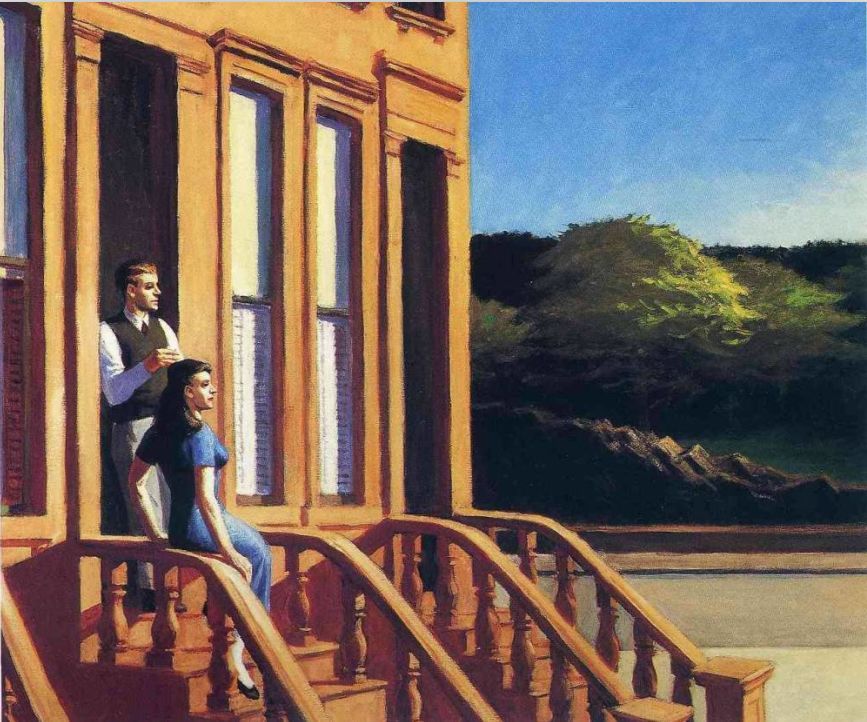
“萨特是对的,热内是个圣人”
我们必须讲述自己的故事,必须建构自己的叙事,从而建构自我的存在。
“这首歌是关于一个女孩,她父亲想让她嫁给一个条件好的求婚者,但她不想。她想嫁给镇上那个醉鬼,因为他能让她夜夜销魂。”这样的讲述可以揭示一切。
我们每个人,都是通过故事来观看这个世界的,自己的故事,或别人的故事。当我们开始讲述时,才能从庸常中跳出来,重新观看这个荒谬的世界。以下两个片段便是明证,哪怕是毫不自觉的讲述,也会反咬住虚伪的表象,逼问出内在的真实。我们缄口不言,我们了如指掌。就像索特开着直升机飞过朝鲜上空,一览无余。
在与达罗夫妇的家庭聚会中,芮德娜怂恿维瑞模仿他在书店里听到的两个人的对话,作为佐餐的段子。
“萨特是对的,你知道。”
“哦,是吗?关于什么?”
“热内是个圣人。”
芮德娜笑了,笑声丰满、赤裸。维瑞为自己模仿得那么像而感到不好意思。在这个十一月的乡村晚宴上,有精美的玻璃杯、鲜花、装饰画,温暖的食物、香烟、炉火,好客的主人和优雅的访客,安逸而又从容。仿佛这才应该是《鲜花圣母》里的场景,像墙上的夏加尔海报一样明亮迷人。
然而,真实的《鲜花圣母》中,“女神”、“鲜花圣母”、“百合花”、“含羞草”,指的都是监狱里的同性恋男人,是不折不扣的“恶之花”。热内这本颇具自传色彩的小说中,充斥着同性肉欲、暴力、污秽与罪恶,“向忧郁的布尔乔亚展示,他们的日常生活遭遇了魅力无穷的杀人凶手”。
从小被父母遗弃,在流浪和盗窃中长大,热内曾先后十次进出监狱,若不是萨特“爱才”,为他求得了总统的特赦,恐怕就要被流放终生了。萨特还为热内的全集写了长达六百多页的序言,即《圣热内》,虽然在桑塔格看来有过度阐释之嫌,但热内的“恶”确实带有某种殉道者的意味,他用罪恶的方式对世界的罪恶展开追问,用荒诞的行为对人的荒诞处境表示决绝的反抗。
的确,这样的晚宴充满了危机,只是当时的芮德娜还没有觉察到。但一经察觉,便无所遁形。从热内和萨特那里,她暗暗学会了如何用生活来对抗生活。
六年以后的感恩节,一场奇异的冬日派对。客人是维瑞的客户们:莱恩哈特医生和他的第三任妻子,魅力四射的四十五岁男人迈克尔·华纳等等。
这次他们谈到的是塞利纳。迈克尔认为他是“一个可怕的男人”,“暴躁、激烈”,但莱恩哈特认为他很“伟大”,于是话题拐到了什么是“伟大”上,医生那位一直盯着迈克尔看的年轻妻子艾达,突兀地开口:“你是对的,塞利纳是个十足的混蛋。”
同样是文明优雅的中产聚会,同样是自传式的书写,我们很难不想到上一次被嘲讽的热内。塞利纳已有中译本的《长夜行》和《死缓》,都是对这个正在分崩离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妙讽刺,短小结巴的句子,破碎杂乱的段落,戏谑粗野的俚语,愚蠢又疯狂的人物。
至少维瑞和芮德娜知道,塞利纳并非无的放矢,婚姻之夜、家庭之夜就是这样虚无,他们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地扮演着各自的滑稽角色。“他们躺在黑暗中,像两个受害者。他们互相无可给予,他们被一种纯粹的、无法解释的爱所束缚……如果他们是另一对夫妻,她会被他们所吸引,她甚至会爱上他们--因为,他们是如此悲惨。”
塞利纳给《恶心》写的题词是:“对集体来说,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男孩,他只是一个个体。”在塞利纳看来,人生就是一次严冬和黑夜中的旅行,人们都在黯淡无光的天空中寻找着自己的路径。索特笔下的维瑞和他的朋友们被联结成了一个集体,“他们所有人,在这片无边无际、覆盖着河流与山丘的蓝色夜幕下。”
这类文学伏笔在《光年》中比比皆是,像一个个兀自旋转着的黑洞,从旁掠过自然无损于航行,只可惜轻易错过了无数光年和多重宇宙。另外一本可供比对的,是索特自己的《游戏与消遣》,偷窥、色情、法国,乍一看来,还以为误入了巴塔耶《眼睛的故事》,也可视作《光年》背后未被讲述的部分。
“早晨一切都不一样,早晨世界是真实的”
日常生活是危险的。最危险的是早晨。“早晨一切都不一样,早晨世界是真实的”。
“完美的一天始于死亡,始于一种死亡的假象,一种深度放弃。……没有善恶之分……它的无限隐藏了他赖以为生的阴谋。”
这是维瑞的视角。
“无论冬夏,只要有可能,芮德娜就会晚起。她真正的自我在床上一直赖到九点,然后醒来,舒展身体,呼吸着新空气。”
这是芮德娜的视角。
“没有幸福像这种幸福:寂静的清晨,来自河流的光,周末就在眼前。他们过着一种俄国式的生活,一种丰美的生活,彼此紧密交织,只要一次厄运,一个失败,一场疾病,就会将他们全部绊倒。它就像件衣服,这生活,外面美丽,里面温暖。”
这是婚姻生活的“真实”。你必须步步为营,枕戈待旦。当我们被迫面对这种“真实”时,恐怕都会震惊于生活本身的残酷与恶心。
索特借帕尔之口,讲了一个富兰克林酒里苍蝇的故事。
“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故事之一……那些苍蝇--挺好--那些苍蝇淹死在酒里,它们和一小点沉淀物待在瓶底,正是这些脏东西告诉你世界是真实的。那就是美国生活中缺少的东西,沉淀物……他把它们放在一个盘子里拿到太阳下晒干……它们复活了。”
很容易就能想到Damien Hirst的苍蝇装置,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,“所有的苍蝇都在这个装置里繁殖、出生、活动、觅食、被电死,成为了一个永久的循环。”有一个朋友评论说,“苍蝇本身不恶心,这种养殖和消灭的循环造成的大量聚集才恶心。”“ 之所以让人恶心,是因为这些你想去回避的场景和想象太司空见惯了。一旦你选择直面,那么可能大多数东西都是恶心的。” 彼得告诉凯瑟琳,“你应该知道,在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有超越纯粹事实的真理。”
在萨特眼中,那些水龙头里汩汩流淌的水、一按开关就会发亮的灯泡、退化到必须用木叉支撑的杂交树木,就像里血迹斑斑的墙壁、屠宰场的腥味和数百万的苍蝇一样“恶心”。他在《恶心》中写道:“是我变了,这是最简单的答案,也是最不愉快的。总之,我得承认,我被这些突然的变化所左右,因为我很少思考,于是一大堆微小变化在我身上积累起来,而我不加防范,终于有一天爆发了真正的革命,我的生活便具有了这种缺乏和谐和条理的面貌。”
芮德娜的生活中,“真正的革命”是由康定斯基与加布里埃尔的分手诱发的。与瓦纳格姆在《日常生活的革命》中的形容如出一辙:“创造生活的意识在增长,因为事物的意义都在说明这一点。各种欲望在回归到日常琐事后,哪一个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大的威力,它正在打破那些让它颠倒的东西,否认它的东西,使它物化成商品的东西。”

“人生可以用伤疤划分,就像一棵树的年轮”
爱情是有时效的,它只茂盛一季,而夏天已经过去。人生也是,“她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所有那些属于过去的都必须被埋葬、抛弃”。她正在进入地下暗河,勇气帮不上忙,智慧也没用。维瑞问她是否快乐,她笑起来。“快乐。她要的是自由。”
“她所说的自由是征服自我。那不是一种自然状态。它只对某些人有意义,他们知道,没有自由的人生不过是吃吃喝喝,直到牙齿掉光,因此,为了自由,他们孤注一掷。”
“日复一日,她塑造着自己的生活,所用的材料是空虚和惊慌,以及如发烧般勇气的阵阵满足感。……这种屈服,这种胜利,让她更为强大……她不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,而且这种快乐似乎并非源于天赐。而是由于她自己的争取,她为此四处搜寻,毫无线索,不惜放弃一切次要之物--即使有些东西无可替代。她的人生属于自己。它不会再被任何人主宰。”
于是我们知道,对芮德娜来说,自由比快乐更重要,因为自由往往来自于对自我的克服,而这个过程,往往是痛的。“人生可以用伤疤来划分,就像一棵树所包含的年轮。”尼洛对弗兰卡说:“毫无意义,你的人生。因为你的人生里没有痛苦。”热内说:“美只源于伤痛。”
“你幸福吗,维瑞?”
“是的,我觉得很幸福。”
“但这难道不是一种很蠢的想法?如果你去真正思考一下。”
幸福,意味着不由自主,意味着对欲望及其后果的无能为力。当我们向往幸福时,就把它悬置在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。用齐泽克的话说,“幸福天生就是虚伪的:所谓幸福,不过是梦想我们实际上并不想要的东西的幸福而已。……真理和幸福并不相容。真理伤人;它会带来不稳定;它会破坏我们日常生活的平稳流动。但选择在于我们:我们是想要幸福地被操纵呢,还是选择把自己暴露在真正的创造性的风险面前?”
是疼痛,而不是幸福,标示了我们的存在。

一条“两边都流”的河
“他们的生活很神秘,就像一座森林。从远处看仿佛是个森林,可以被理解,被描述,但靠近了它就开始分离,开始破碎成光与影,让人目眩的茂密。在它内部没有形状,只有四处绵延的大量细节:奇异的声响,几缕阳光,枝叶,倒下的树,被树枝折断声惊逃的小兽,昆虫,寂静,花朵。”
做衬衫的人认为,“细节就是一切”。这让维瑞和阿诺德都为他痴迷。他们认为,文明就维系在这样的人身上,就像十二圣徒。但索特堆砌大量的细节,绝对不是在全然歌颂生活和细节,而是在竭力铺陈背景,设置等待被点亮的对象。从他的讲述中,我们能够分辨出,哪些是难以忍受的冗杂庸常,哪些是主动拥抱的真实生活。
抱着狗的没牙老太婆、手术割掉一条腿的小女孩、满身呕吐物的流浪汉,都不重要,不存在,没意义。有意义的是你是如何意识到他们的存在,又是如何意识到作为观看者的自己的存在。
到最后,我们发现“日常生活颂歌”其实是“个体的颂歌”。重要的不是细节本身,而是观看细节的我们。重要的不是生活的质料,而是你如何去生活。“我哪儿也没去过。但我什么都干过,那更重要。”
最后,让我们来检验一下,20年的时光改变了什么:
“钱。我想要很多钱。我从未有过足够的钱……我喜欢衣服和美食,我不喜欢巴士或低等场所。钱真的很妙。我本该嫁个有钱人。维瑞永远不会有钱。”
“我知道我会贫困而死……身无分文。变卖一切--珠宝、衣服。他们会跑来拿走最后一点家具。
这是芮德娜的变化。”
“他相信伟大。似乎伟大是一种美德,似乎伟大会为他所有。……他想要一样东西,一种可能性:出名。他想要成为人类大家庭的中心,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期求、渴望?”
“这没什么价值的一生……如果当初我有勇气,他想,如果当初我有信念。我们总想着不朽,似乎那很重要,不惜以他人为代价,我们只顾自己。……然后我们一路向前,紧追不舍,直到再也没有别人--只剩下我们自己,除了上帝,再也没有别的同伴。而我们并不相信上帝。我们知道他并不存在。”
这是维瑞的变化。
存在两种生活:一种,是人们相信你在过的生活;另一种,是我们渴望去过的生活。
存在两种自我:一种,是被呈现和表述的自我;另一种,是我们不断成为的自我。
存在一条“两边都流”的河:一边,漫过时间的堤岸,冲刷又重塑着我们的记忆;另一边,勇往直前,不知疲倦地讲述着我们的存在和未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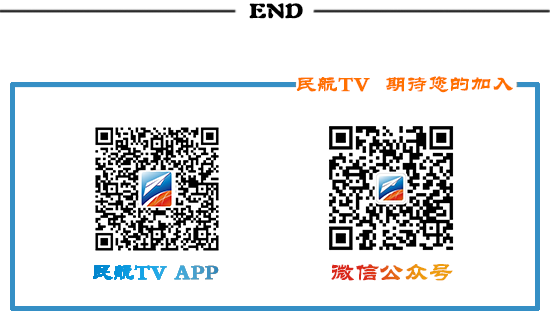
我要评论